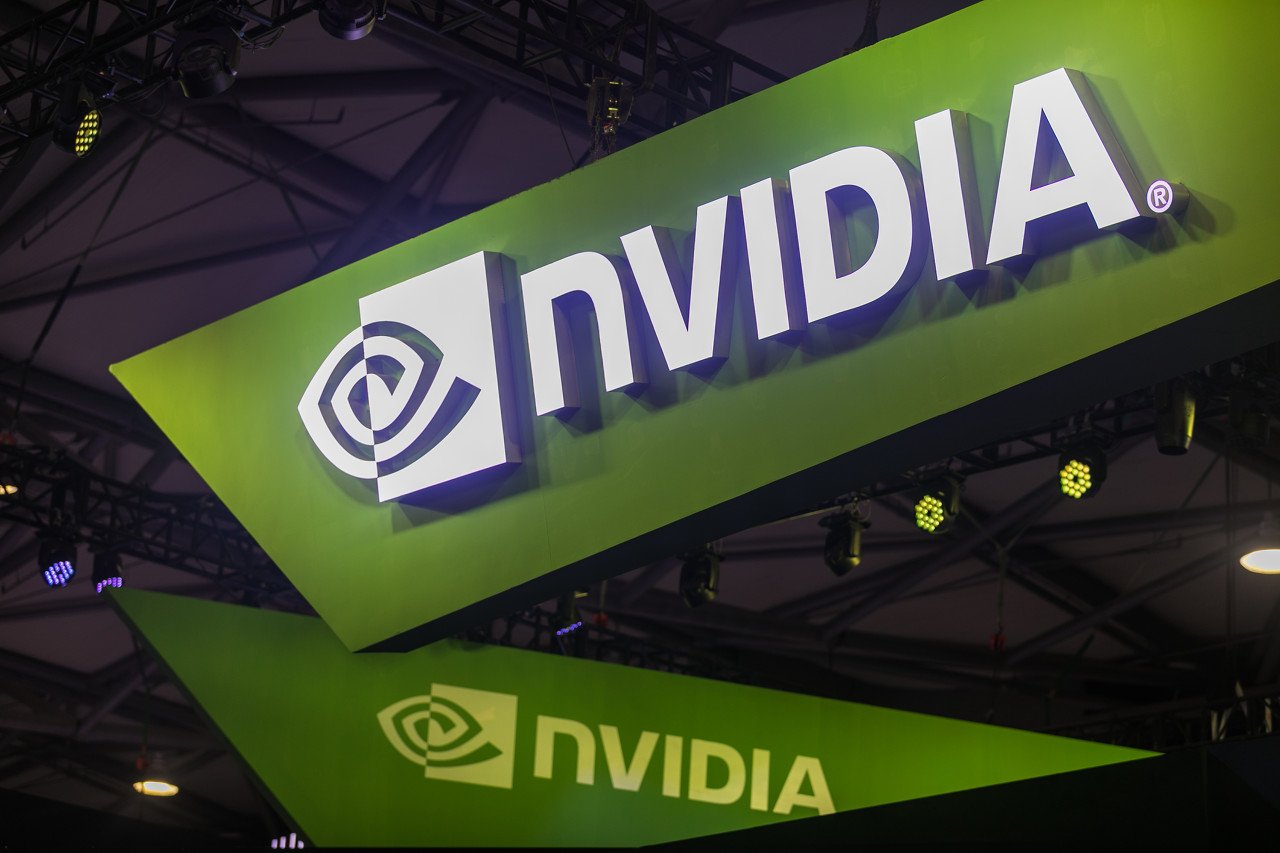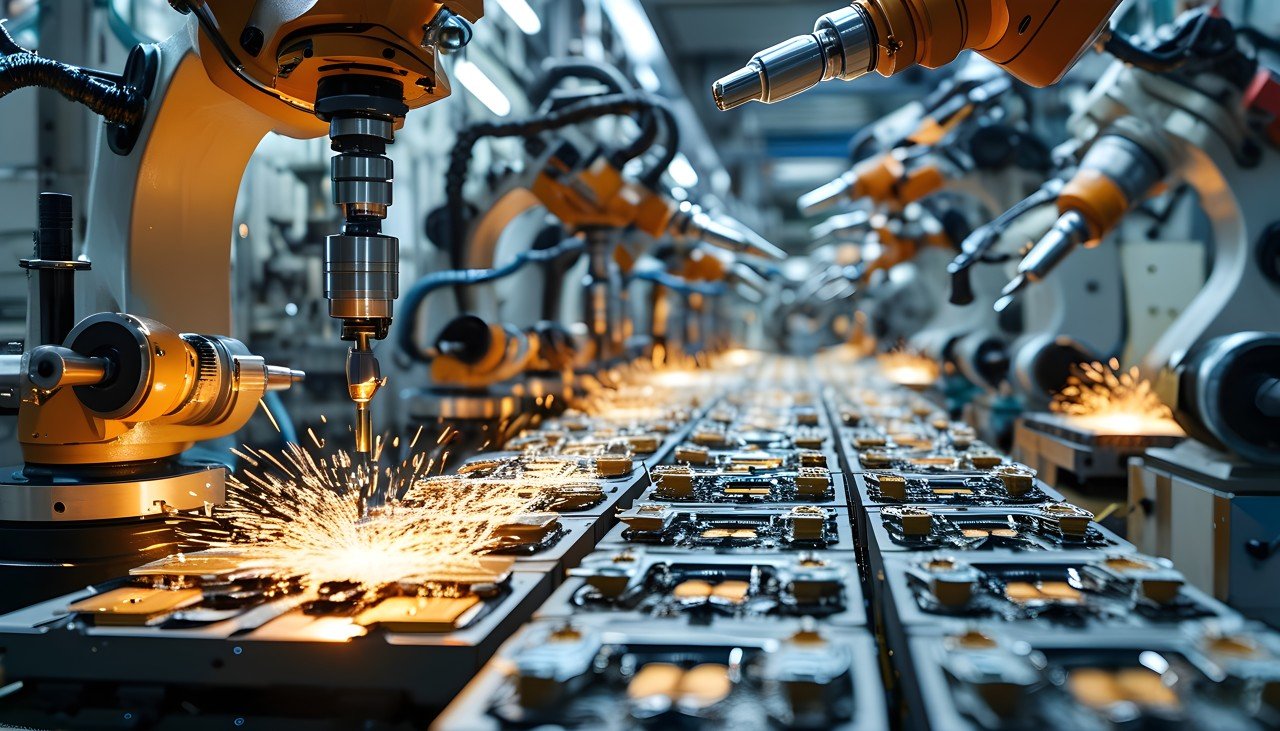管濤:人民幣匯率有基礎有條件保持基本穩定
把握好內外部均衡的平衡是我國貨幣政策主要目標之一。2022年和2023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連續兩年提出要“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這是自2015年“8·11匯改”以來的第二次(第一次是2016年和2017年)。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更是將“加強外匯市場管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列爲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金融工作的一項中期優先任務。
現階段人民幣匯率影響因素多空交織
從今年情況看,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主要是國內經濟修復、海外貨幣緊縮及央行匯率調控情況,人民幣強弱將取決於國內經濟修復的利好能否對衝美聯儲緊縮政策和美元強勢的利空。
進入2024年,一方面,國內經濟基本面改善對人民幣匯率的支撐加強。一季度經濟增長超預期,外需回暖帶動工業生產和制造業投資較快增長,居民收入和就業狀況好轉驅動最終消費需求繼續恢復,促進經濟回升向好的積極因素進一步累積。另一方面,美聯儲寬松預期回撤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偏空。由於前3個月美國通脹數據連續超預期,美元指數和美債收益率止跌回升,非美元貨幣繼續承壓。進入4月份以來,日元、韓元、印度盧比等亞洲貨幣對美元匯率均刷新近年來甚至幾十年來的低點,人民幣匯率承壓也反映了強美元的負溢出效應,但人民幣在主要貨幣中的表現依然相對堅挺。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日元匯率連創34年來新低,但當前的局面與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有着明顯不同。一方面,與20多年前相比,亞洲地區經常項目收支平衡、匯率政策靈活性提高、外匯儲備增加、外債規模和結構趨於合理,對於強美元周期的外部衝擊承受力明顯改善。另一方面,與20多年前相比,日本與中國在亞洲地區的經濟和金融影響力此消彼長,人民幣成爲越來越多亞洲貨幣的名義錨,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扮演着亞洲貨幣“穩定器”的角色。
外匯市場韌性是我國穩匯率的底氣
隨着美國經濟“不着陸”的概率上升,美聯儲更遲、更少降息的預期將繼續成爲2024年人民幣匯率的“逆風”。2015年“8·11匯改”時,部分受累於中美貨幣政策分化,中美正利差收窄,人民幣匯率持續承壓。2015—2017年人民幣匯率連跌3年,累計跌幅近9%。這一次,中美貨幣政策再次錯位,中美負利差擴大,2022年和2023年人民幣年均匯率連跌兩年,累計跌幅也達9%。目前看來,2024年是人民幣匯率延續調整的第3個年頭。
人民銀行多次強調,人民幣匯率有基礎、有條件保持基本穩定。經濟強則貨幣強。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是穩匯率的關鍵。與此同時,在堅持匯率由市場決定的前提下,不斷完善匯率調控,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也是在爲經濟調整爭取時間。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從價格維度看,當前外匯市場壓力與“8·11匯改”初期相似,但從數量維度看,外匯市場基礎卻是今時不同往日。
一是“8·11匯改”前,自1994年初匯率並軌後,人民幣經歷了20多年的單邊升值行情,市場主體對於人民幣貶值既無心理也無措施上的准備。但2015年匯改後尤其是2019年8月人民幣匯率破“7”之後,人民幣匯率已多次跌破又升回到“7”以內,匯率雙向波動常態化,市場對於匯率漲跌不會過度關注。
二是“8·11匯改”前,在長期單邊升值行情下,形成了民間資產本幣化、負債外幣化現象,積累了巨額的對外淨負債。“8·11匯改”初期,人民幣意外貶值觸發了市場主體集中增加海外資產配置和償還對外債務的順周期操作,令我國遭遇了“資本外流—儲備下降—匯率貶值”的高烈度跨境資本流動衝擊。但經歷了那波集中調整後,截至2023年底,民間對外淨負債降至5415億美元,較2015年6月底(“8·11匯改”前夕)大幅減少1.83萬億美元。民間貨幣錯配明顯改善,顯著增強了市場主體對於人民幣貶值的承受力。2019年8月以來,人民幣匯率多次圍繞“7”上下波動,外匯市場保持平穩運行,經受住了考驗。
三是隨着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提高和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境內市場主體越來越多地運用本幣計價結算和外匯衍生品工具規避和對衝匯率風險,對匯率波動的適應性和容忍度也明顯增強。受益於此,近年來境內外匯市場總體呈現“逢高結匯、逢低購匯”的運行特徵。
國家外匯管理局相關負責人多次指出,我國外匯市場運行展現出較強韌性,市場預期和交易保持理性有序。這是基於數據作出的專業判斷。如2023年是本輪人民幣匯率調整的第二年,從銀行結售匯和跨境資金流動狀況看,較上年確實出現了一些新變化,銀行結售匯和銀行代客跨境收付均出現2019年以來首次逆差。但是從可比口徑看,2023年,銀行即遠期結售匯逆差436億美元,遠低於2015年、2016年分別5712億和3695億美元的規模,也低於2017年893億美元的規模;銀行代客跨境收付逆差687億美元,2015—2017年分別爲1940億、3053億和1245億美元。這反映出當前外匯供求失衡的程度和資本流動衝擊的烈度遠不及彼時,我國外匯市場已經逐漸走向日益成熟。至於將人民幣升貶值等同於升貶值壓力和預期,是缺乏國際金融常識的表現,是對匯率市場化的嚴重誤解。匯率市場化是要讓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正常情形下應該是“高(升值)拋低(貶值)吸”。恰恰是匯率僵化才會積累單邊壓力、強化單邊預期。若在匯率波動中出現這種情形,意味着市場出現了順周期單邊羊群效應,央行要實施必要的幹預。
從國際收支視角看人民幣匯率
銀行結售匯和銀行代客跨境收付數據都是中國特有的外匯收支統計指標體系,國際收支數據則更加具有國際可比性。從國際收支口徑的數據分析,也可以爲前述結論提供支持。
市場曾擔心人民幣貶值會加速資本外流,但實際上2023年中國資本外流壓力不是發散的而是趨於收斂。2023年,中國國際收支口徑的資本項目逆差2482億美元(含淨誤差與遺漏),同比減少18.7%。其中,短期資本淨流出1056億美元(又稱非直接投資形式的資本流動,含淨誤差與遺漏),減少67.7%。其背後是匯率下跌對於資本流動“獎入限出”調節作用的正常發揮。現實中,跨境資本流動有內資(即對外投資,對應非儲備性質金融账戶的資產方)和外資(即外來投資,對應非儲備性質金融账戶的負債方)兩個主體。2023年,中國民間資本項目(即非儲備性質金融账戶)淨流出2099億美元,較上年減少18.4%。其中,民間對外投資淨流出2234億美元,減少6.4%;民間外來投資淨流入134億美元,上年爲淨流出187億美元。
拉長時間看,前述結論同樣成立。2022—2023年,中國資本項目年均逆差2768億美元,較2015—2017年均值下降39.3%;短期資本年均淨流出2163億美元,下降54.4%。同期,民間資本項目年均逆差2336億美元,較2015—2017年均值低了5.4%。其中,民間對外投資年均淨流出2310億美元,較2015—2017年均值低了48.3%,較2020—2021年(上輪人民幣匯率升值期間)均值低了65.9%。這反映出在本輪人民幣匯率調整中,境內市場主體預期保持了基本穩定,同時前期“藏匯於民”政策對於平滑資本流動順周期的波動起到了“蓄水池”作用。而2016年底市場激辯保匯率還是保儲備時,當年民間對外投資淨流出6756億美元,較上年增加1.02倍,外來投資由上年淨流出轉爲淨流入2596億美元。顯然,當時穩匯率的關鍵在於穩住在岸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2017年,人民幣匯率不僅沒有破“7”,反而上漲6%以上,重挫了做空人民幣的勢力,重塑了匯率政策公信力。
民間對外淨負債銳減大大約束了貶值壓力下金融交易項下的實際用匯需求。受益於此,2024年3月,境內人民幣匯率異動,境內外匯供求缺口擴大,但這主要是因市場結匯意愿減弱,而非購匯動機增強。此外,今年前3個月與2023年最後兩個月(人民幣止跌反彈期間)相比,市場結匯意愿上升、購匯動機減弱, “低(升值)买高(貶值)賣”的匯率槓杆調節作用仍在正常發揮。
從國際經驗看,貨幣攻擊得手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本國居民和企業恐慌性地搶購和囤積外匯。顯然,我國並沒有出現這種情形,這是近年來境外勢力做空人民幣卻屢屢無功而返的重要原因。中國經驗再次表明,只有國內經濟金融體系健康,才能充分享受匯率浮動和資本流動帶來的好處。加之中國經歷了多輪資本流入和流出、人民幣升值和貶值的切換,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不斷完善,積累了豐富的匯率調控經驗。這正是我國有信心、有能力、有條件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底氣所在。
注:本文發表於《中國財經報》,作者: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
標題:管濤:人民幣匯率有基礎有條件保持基本穩定
地址:https://www.iknowplus.com/post/1120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