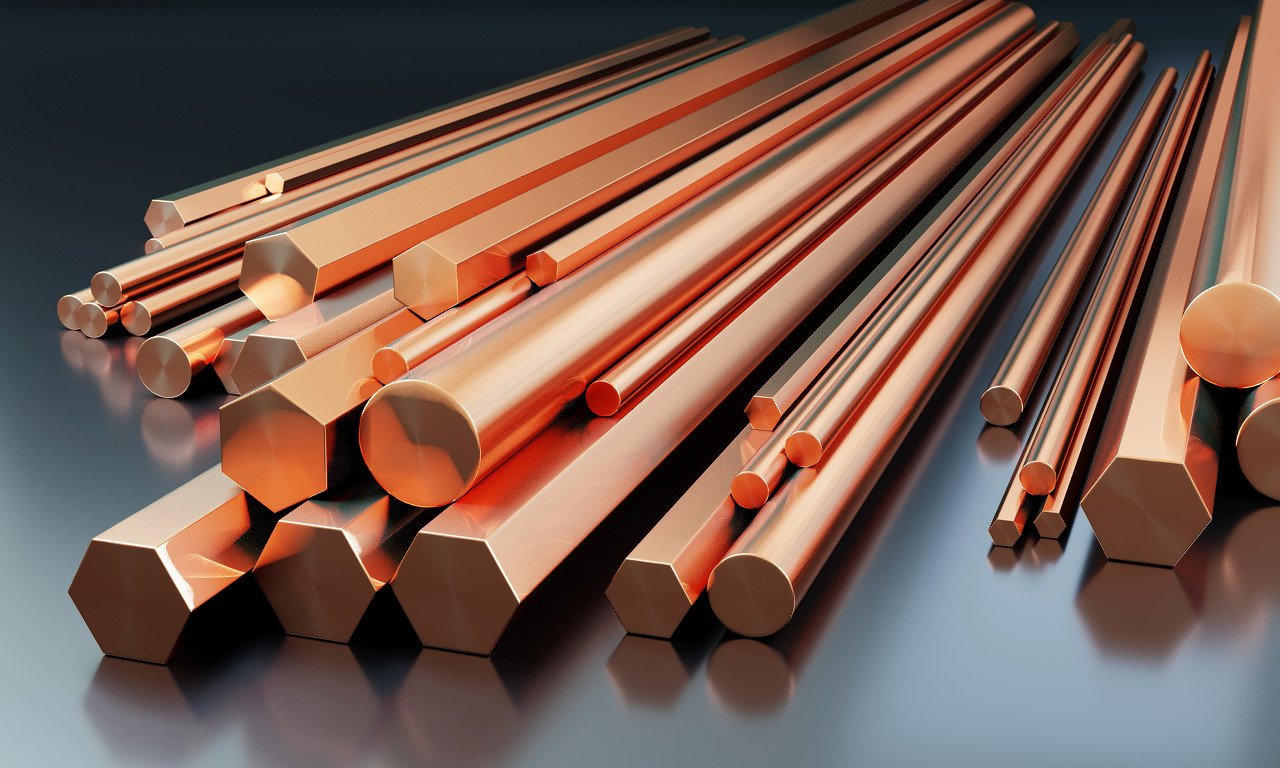中金:在中國保障房市場行將演進之前的一些思考
中國政府擬推動保障性住房建設進一步發展[1],這也是中國大陸房地產行業構建“新發展模式”的關鍵領域之一。目前,因具體的制度設計可能尚在形成之中,對於未來可能的政策取向市場或許存在不同的看法。我們在本篇報告中,結合對海外市場的歷史經驗辨析,對於怎么看待中國大陸發展保障房,以及可能面對的一些內在命題,先做初步的討論。
摘要
從全球背景看,中國大陸住房政策的邊際調整並不突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普及,助推了住房的商品化以及房地產金融的繁榮發展,但也造成住房可負擔性總體上已經處於過去40年來幾乎最低的位置,或暗含了公共政策的拐點將至。看待中國大陸的情形也有類似之處,即我們在過去20年走過了一個相對單邊的住房市場化過程,也積累了一些矛盾,眼下市場與保障的天平需要向另一側回擺,其實不難理解。
“學新加坡、學中國香港還是學其他市場”,是否需要有此一辯?我們認爲更有價值的是辨析出一些海外市場的路徑成因,而非簡單借鑑某種模式,事實上即便面臨近似的市場矛盾,每個經濟體的政策選擇都可能差異顯著,住房體系的調節最終都是一個高度本地化的過程。如一定要做一個比較,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從土地制度上與中國大陸更爲接近,對於房地產市場的管理方式也更重實物調節,但新加坡、中國香港的做法與效果卻是大相徑庭。我們認爲中國大陸現面臨的市場矛盾可從中國香港的歷史中窺見較爲類似的情狀,但“學習中國香港”恐非我們所愿。既然如此,新加坡的產品設計是否有條件在中國大陸落地?或也非那么簡單。那么美、日、歐呢?公共住房在這些經濟體中過去40年整體是愈發邊緣化,這可能不是我們要的方向。但至於是否存在一些可借鑑的經驗,有些方法未嘗不可研究。具體內容,請投資者參考正文,我們尤其對新加坡、中國香港兩地經驗做了較深入的討論。
中國大陸住房體系的調節或需要創造性思維,理順保障與商品的關系。淺談幾點:第一,在住房供求關系已經發生重大轉變下,對於增加無論何種形式的供給都需謹慎;第二,我們認爲保障性租賃住房的制度設計已漸趨完善,未來的重點在於購置型產品的設計;第三,當仔細考慮“雙軌制”的內涵,我們從海外市場比較成功的實踐經驗來看,一個重要的點,是在產品設計上,盡量避免將“保障”和“商品”對立起來(比如新加坡的組屋就是一個兼具雙重屬性的產品),否則將制造更多的管理難題。到中國大陸市場,對於購置型產品,理順“保障”與“商品”的關系或是未來的核心命題。
風險
中國大陸保障房領域制度建設遲緩;住房可負擔性進一步下降。
看待中國大陸住房政策調整的背景
在全球背景下看中國大陸住房政策的邊際變化並不突兀。我們認爲很重要的一點是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普及,助推了住房的商品化以及住房擁有率的提升,也令金融在過去40年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發展。住房商品化在很多地區被視作一種經濟發展手段,但造成的隱患越來越大,於住房本身,這表徵爲當前全球住房的可負擔性總體上處在幾乎過去40年來最低的位置,可能也暗含了公共政策的拐點將至。
看待中國大陸的情形也有類似之處,即我們在過去20年走過了一個相對單邊的住房市場化過程,但眼下市場與保障的天平需要开始重新向另一側回擺,中國政府將保障房的建設置於更加突出的位置,其實不難理解。
中國大陸如要進一步推動住房改革,可能面臨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一是應對金融波動對住房供需的衝擊(中短期),二是處理好保障房與商品房市場的關系(長期)。在當前商品房供需雙趨弱的背景下,以新的保障房建設來彌補潛在缺口,可能是我們初步確立的政策意向。那么下一步更關鍵的頂層設計問題,便來到雙邊市場的關系該如何考慮,以及如何管理市場。
怎么看海外市場,尤其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經驗?
中國大陸的挑战是否能從國際經驗中找到既得解法?沒有特別直接的路徑參考,因爲中國大陸面對的情形是在高住房擁有率和高度商品化的背景下,來進一步完善公共住房體系,這與過去40年的主流敘事(即推動商品化和私有化)在方向上並不一致。在不少西方市場(包括日本),公共住房在過去40年逐漸邊緣化,顯然不是太值得參照的案例。
對中國大陸設計公共住房市場而言,我們認爲目前最具研究價值的還是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這二者也是全球少數至今仍維系着規模較爲龐大的公共住房市場的經濟體,並在城市的尺度上提供了豐富的經營細節。
爲什么說新加坡、中國香港可以提供最直接的經驗參考?首先源於土地公有制這一基本制度的相似。在應對住房問題時,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土地公有制經濟體和西方典型私有制經濟體之間的基本方式差異。簡而言之,土地公有制經濟體更傾向於借由公共部門之手直接調節實物供需關系,往往涉及對住房產品和購房政策的動態調節,是之謂“主動管理”。
考慮到住房在這些經濟體居民家庭財富中長期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政府要持續做主動管理便不難理解。反過來想,對實物供給的直接幹預,也是土地公有制行事的“便宜之處”。西方市場的政府部門相對“較小”,缺乏相應的實體資源和專業性來直接調控市場,因此我們看到西方市場的政策調節往往集中在金融、貨幣和財稅領域,通過對收益率的調節,動員私人主體去達成政府的某些公共目標。
由於這種方式主要是間接的,而且很難保證市場與政府的目標始終一致,因此未能取得太好的成效,這或許也是西方市場公共住房規模逐步衰減的內在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新加坡、中國香港的公共住房體系均已具備近60年的主動管理與運行歷史,兩者官方統計機構數字顯示目前分別承載了當地約80%和50%的家庭戶,可以爲中國大陸設計公共住房市場提供最直接的參考。
如何考慮保障與商品、公共與私人市場的關系?新加坡、中國香港兩個經濟體給出了不同的詮釋。新加坡的組屋,實際上集保障與商品屬性於一身,體現爲一級市場購置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與政府補貼,但二級市場的轉售價格則由市場供需來決定,一二級往往存在可觀的價差。
因此,新加坡的組屋本身並不存在保障與商品的內在矛盾,而至於組屋(公共住房)與私人住房的關系,則主要是依據居民收入水平來做市場准入的隔離。但因私人市場的份額較小(約20%),且主要面向高收入群體,故不構成政府管理的重點,也很少造成實質的社會矛盾。但如若我們去考證私人住房與組屋轉售市場的歷史價格變動趨勢,可以發現二者也沒有什么顯著的不同。
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共住房(組屋)與私人住房的財產屬性沒有太本質的差異,更多體現在房屋質量和面積有所分層。中國香港的公共與私人住房市場,也即保障與商品市場,則是一個更具平行特徵的模型。公共住房中又分爲公屋(廉租)和居屋(共有產權房),中國香港統計處數字顯示分別佔31%和15%的住房市場份額(截至2022年)。居屋理論上是一個可以兼具保障與商品屬性的產品,但與新加坡很不同的是,中國香港居屋在一級購置端盡管較市場價格有一定的折讓,但購得的產權並不完整(通常只有70%),如若居屋持有者希望所持物業可以作爲普通商品房出售(否則就只能在居屋第二市場這一封閉市場內以相對較低的價格轉讓),則需要在後續擇時補完地價以獲得完整產權。
歷史上完成補價的戶數不多,我們統計2005年至今完成補價的居屋戶數累計僅佔居屋存量單位數的6%左右,而且2010年以後,因房價加快上漲,能夠補價的人數較00年代又大幅減少。居屋和私人住房在資產增值能力上的這種不對等,可能也對於居民攀爬住房階梯構成一定的困難,這也是其和新加坡組屋的一大關鍵差異。
中國香港更重要的部分或許是公屋,我們統計公屋的平均單平米租金僅爲私人單位的20%左右,帶有明顯的福利性質。在中國香港整體租賃市場中,公屋佔約三分之二的份額。
至此,我們大致介紹了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兩地的住房體系特徵差異。
如果說新加坡的住房體系帶有更加普惠和相對均等的特徵,那么中國香港的公屋—居屋—私人住房三級體系,看起來是一個內部高度分化分層的體系。
直觀的比較兩種體系的結果,中國香港住房市場的矛盾更多可能是衆所皆知的,包括高房價(從房價收入比的角度來看,中國香港私人住房是新加坡組屋的3-4倍)、住房擁有率出現瓶頸(長期停留在50%附近)、公共住房輪候時間不斷攀升、人均居住面積的狹小等等。
中國香港住房體系的設計是否要爲其住房矛盾負責?我們認爲中國香港住房矛盾有其深層次制度根源,而不論是市場更多關注到的供給不足的問題,還是住房結構本身的動態調節,都是應對環境矛盾而形成的“果”,不是“因”。一個極簡的表述是,中國香港的土地財政制度有強化私人住房市場的內在動力(以實現財政、經濟、金融的共榮),住房供給中公共與私人各半的這種貌似均等的呈現,是一種制衡的結果。但公共住房的制度調節在歷史上更爲頻密,總體上還是爲了平衡其與私人市場的關系,在維系基本社會民生目標與防止侵佔私人市場利益之間做周期性的擺動。我們無意詳述歷史,這裏舉兩個簡單例子。
比如70年代公共住房的供給起初是面對一般工薪階層(與英國的早期設計類似),其內涵不是低收入住房,但之所以今天已經廣泛成爲低收入群體的聚居區,和80-90年代开始實行的“富戶政策”[2],將超過一定收入水平的住戶引導出公屋有關。此處的重點,不是討論該政策的適當性,而是注意到歷史的不同選擇,比如英國也曾有相似的住房格局,但其在70年代开始推行“購房權”計劃,推動公共住房住戶买斷其房屋產權,轉性爲私人住房。
這一私有化進程,實際爲居民家庭創造了真正的財產,新加坡組屋轉售市場的建立與完善,其實也是一個賦予財產屬性的過程。這個過程中間是否有財政端的潛在損失?顯然是有的,甚至是不小的。
但中國香港不愿意賦予公共住房以真正的財產權益,我們認爲可能相當程度上是出於防範衝擊私人商品市場的考慮,這從我們上邊提到的居屋補地價的政策中也可以窺見一斑。第二個例子更直接,2002年开始中國香港爲托舉私人住房市場,將居屋供給叫停,直至2011年才復建。
同期,中國香港在這十年內的住房土地供給變得非常稀缺,也是一種較爲極端的供給端政策。但不供房不賣地拖垮了財政嗎?事實上2003年之後伴隨房價修復,除賣地以外的房地產相關收入(比如交易環節稅收)出現明顯回升。
2010年後隨着房價上漲速度進一步加快,賣地收入迅速擴張,大幅充盈了港府的財政儲備。
所以歸根結底,中國香港至今仍在努力維持一個穩定規模的公共住房市場,是一個財政與民生平衡的結果,以及從歷史中考證,對公共住房供給的調節,穿透來看背後可能也有財政管理的考慮。
中國香港“住房階梯”的攀爬通暢嗎?應該說伴隨一個個體勞動者年齡、收入的增長與需求的變化,從租到購、從剛需到改善的需求路徑可能是切實存在的,因此爲了滿足不同階段、不同層次的住房需求,搭建“住房階梯”這一初心本身沒有問題。比較關鍵的,其實在於對不同住房產品的“觸達性”(Accessibility)是否通暢。
中國香港體系給我們的一個啓示是,如果公共與私人市場之間本身存在一定的內生博弈關系,那么在制度設計上容易將保障與商品做一定的隔離,可能不利於住房流轉的效率。例如我們測算2015年來每年公屋遷出的戶數佔總公屋戶數的比例在1%左右,其中遷出去購买居屋的比例平均在35%左右。
居屋方面,居屋第二市場的成交套數佔存量的比例平均每年在0.6%左右,完成補地價的人數在0.1%左右。相比之下,新加坡組屋二級市場的交易套數佔存量的比例近年來平均在2.5%左右。總體上確實很難認爲中國香港住房市場的流轉是活躍的。
在“觸達性”這一點上,可能西方市場以財政補貼租房人和購房人,令消費者有更多自由選擇的權利,對於資源配置的扭曲就相對會小一些。
新加坡的做法,是基於收入、家庭戶人數、公民身份等條件審查,將需求做較爲嚴謹的切分,並有計劃的針對不同群體來提供不同的產品(如兩居、三居還是四居),也會有意識的促進住房流轉。
但這種做法的一個可能不甚效率的地方在於,供給調整往往滯後於需求的變化。以及在供給權主要掌握在政府而不是市場手中的情況下,對政府相關機構的專業能力要求就變得非常高。
新加坡模式看起來成效更佳,但其成功的核心要素與可模仿性有多大?我們認爲新加坡的相對成功主要有賴於兩點。第一是強有力的政府機構;第二是其制度設計上,組屋很好的解決了保障與商品的博弈問題,正體現了“簡單的設計才是好的設計”。但從可模仿性來講,更難的是前者,這至少包括是否具備高度專業的領導機構(以研究、統籌、設計、監督各項事務)、該機構是否具備對多线條多部門的協調能力、是否具有強大的落地執行能力、是否可以保持機構的政策公正性、以及機構在預算平衡角度能否獨立可持續運營等等。
以上這些能力的建立,首先需背靠強有力的政府部門,其次需要不菲的政府資源投入(包括人、地、錢),最後,必須經過長期發展磨練以真正做到政策的因地制宜。從全球範圍來看,幾乎可以認爲大部分經濟體都不存在模仿的基礎,但中國大陸或許具備一部分先天要素,以及一定的相關實踐基礎。
除了新加坡、中國香港之外,其他市場還有沒有優質經驗?我們認爲英國的租戶分步購置房屋制度,美國的可負擔性住房稅收抵免制度(LIHTC),都是很有創造力的制度,分別給了購房人和开發商一定的靈活性。
日本雖然沒有發展出成規模的公共住房市場,但日本的私人租賃市場發達,也起到了一定的社會住房效果,不失爲一種方式。德國的租賃與購房補助制度,也是學界討論較多的方面,但我們也需注意德國的住房擁有率長期較低(低於大部分發達國家)[3],這是否是我們想要的邊際方向,值得商榷。
但總體而言,這些優質經驗的共同特點,是沒有把保障和商品的供給對立起來,也沒有把公共和私人市場的運行完全隔離开來,這樣政策就可以借助一部分市場的力量來共同實現目標的調節。以及,這些政策都是在各經濟體自身的政治經濟語境下產生的獨具特色的實踐經驗。
如何考慮中國大陸自身的方向?
回到中國大陸,如何考慮我們的潛在路徑選擇?在談論未來之前,可能先釐清一些我們當下的約束條件是必要的。首先,我們已經實現了城鎮範圍內較高的住房擁有率和商品化率,意味着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即便保障房的邊際供給佔比明顯提高,從總量上來講,它仍是一個規模次於商品房的、補充性的市場。
因此,在住房總體供求關系已經發生重大轉變的背景下,可能接下來的主要問題要落於保障房的角色定位與產品創新。在這方面,我們認爲“租購並舉”的頂層設計首先將延續,中國大城市的租賃佔比明顯低於國際市場的普遍水平[4],這意味着我們在居住形式的選擇上仍需要做更好的平衡,這也確實需要從供給側發力。
落於具體產品的層面,2020年以來加快發展的保障性租賃住房,在產品定位、供給機制、籌措目標、投融資模式等方面都已經有相對成熟的實踐經驗,未來的路徑也比較清晰。更需要做進一步探討的,可能是在購置型這一端,產品的設計還有沒有調整的空間。
中國大陸如何在購置型產品的設計上借鑑新加坡、中國香港經驗?中國大陸在購置型的保障房領域先後經過了00年代的經濟適用房以及10年代的共有產權房、人才房、兩限房等等,產品形式多樣但總體的供給量和商品房相比不算太多。共有產權房的設計與中國香港的居屋比較相似,在中國各地實踐中可能呈現出一定的房屋質量不高、退出機制不暢等情況,因此目前市場關心的可能更多是如何借鑑新加坡經驗。
首先,新加坡組屋市場可以認爲是“封閉管理”的,這也是目前中央已經明確提出的針對保障房市場的原則要求,我們認爲“封閉管理”意味着對前期購房准入、期間運營管理、以及後期流轉退出做閉環管理,確保市場有序運行。組屋的一些其他產品要素包括構建在公積金系統上的優惠利率貸款、限購、限售條件等,這些要素對中國大陸市場而言並不陌生。
簡而言之,我們認爲狹義的模仿新加坡組屋的產品設計本身或許並非難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這類市場作爲住房的主要市場和次要市場,可能在效果上會有什么不同?如果是作爲補充型市場來建設,中國大陸是否會首先陷入(我們在上文分析過的)類似中國香港在制度設計上遇到的一些困擾(比如和商品房市場的互動關系)?組屋的精髓或許在於保障與商品屬性的集成,以及相對自由的退出機制,而組屋和居屋在退出端的約束程度不同,某種意義上其實可以理解爲是公共住房作爲主要市場和次要市場最重要的內生差異。
在這一基本矛盾下,中國大陸的保障房究竟是否可以做到真正的“新加坡模式”?以及如若照這一模式推廣,保障房在退出上幾乎與商品房平權,會不會產生一些負外部性,比如影響到商品住房的需求格局,以及購房公平(考慮一級購置可能涉及補貼)?
如果擔憂這些因素,在退出端做更封閉保守的處理,那么這個次要市場會不會有足夠的流動性?以上更多代表我們現階段的一些疑慮與思考,我們也希望能夠借此報告來拋磚引玉。
是否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思路方向?我們認爲陷入到借鑑新加坡還是中國香港的討論當中其實沒有太大必要,這些經濟體的經驗主要是爲我們看待制度內生矛盾提供一些視角。
回到中國大陸的基本形勢,首先是我們住房總體的供求關系已經發生重大轉變,因此我們認爲思考購置型產品的一個出發點,是不去增加不必要的供給,引致保障與商品房競爭的風險。我們認爲應該警惕,如若商品房的市場份額受到進一步擠壓,或將給我們防範處理房地產領域金融風險帶來更復雜的局面。
其次,在產品設計上,我們可能也沒有必要先入爲主的將其與商品房對立起來,這不是“雙軌”的必然含義。比如我們是否可在保障性租賃住房的基礎上考慮購置權的引入,允許先租後买;又比如我們是否可以將思路從實物供給延伸至貨幣支持,給特定收入水平的群體提供一定的購房補貼或信貸優惠,讓其在現有市場上自由選擇購置目標(這在國際市場上其實也很常見)。
以上不構成嚴格意義上的政策建議,而是想表達思路範圍或許還可以進一步打开。最後,我們認爲不同路徑方案所需要的政府部門的資源投入力度也是迥異的,潛在執行層面的可行度,或許也是一個需要評估的方面。
我們將持續高度關注中國大陸保障房政策的演進。最後,回到討論的原點,我們認爲當前中國大陸(以及國際市場整體)住房領域的共同挑战是“可負擔性”,我們認爲中國大陸將保障房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大勢所趨。以及對中國大陸而言,住房體系的調整在中短期維度需要兼顧房地產領域金融風險的管理。而中長期維度住房體系的重新穩定,則可能是推動財稅、土地、金融等更多深層次制度改革的前置條件。伴隨未來中國大陸新的保障房政策體系可能進一步明朗,我們將持續關注該領域的變化與潛在影響。
風險提示
中國大陸保障房領域制度建設遲緩。中短期維度,住房體系的調整需要兼顧房地產領域金融風險的管理;中長期維度,住房體系更是與財稅、土地、金融等更多深層次制度改革密切相關。
住房可負擔性進一步下降。若保障房相關制度或建設進度偏慢,住房可負擔性存在進一步下降的可能。
本文摘自:2023年12月15日已經發布的《在中國保障房市場行將演進之前的一些思考》
孫元祺 分析員 SAC 執證編號:S0080521050008 SFC CE Ref:BOW951
張宇 分析員 SAC 執證編號:S0080512070004 SFC CE Ref:AZB713
李佳璠 分析員 SAC 執證編號:S0080523120001 SFC CE Ref:BTL933
曠美琦 分析員 SAC 執證編號:S0080523070022
王翼羽 分析員 SAC 執證編號:S0080521050007 SFC CE Ref:BOR985
程堅 分析員 SAC 執證編號:S0080522080011 SFC CE Ref:BSB850
標題:中金:在中國保障房市場行將演進之前的一些思考
地址:https://www.iknowplus.com/post/630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