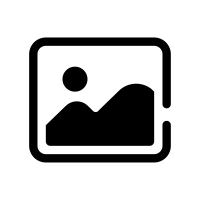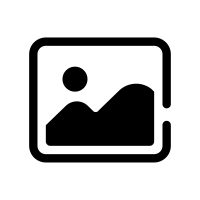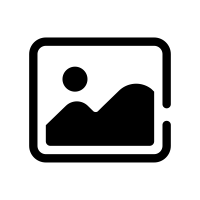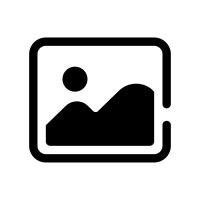走出低通脹:“去產能”和“促消費”誰更有效?
核心觀點
核心觀點:去產能政策常被當做是提振物價的不二之選,但是對當前價格周期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去產能,而是擴大消費需求,以促進服務價格回升。這是因爲,服務價格降至歷史最低水平,才是本輪低通脹的核心症結,而去產能政策通常只能帶動工業價格回升,對服務價格無濟於事。假設採取去產能政策,使得短期工業價格在2024年的基礎上回升2個點,GDP平減指數將從2024年的-0.7%回升到-0.02%,仍不足以走出低通脹;但如果促消費政策力度更大,使得服務價格回升同樣2個點的幅度,GDP平減指數將從-0.7%回升到+0.39%,加上消費回暖帶動的商品價格回升,最終GDP平減指數還會更高。
1、從供需對比來看,本輪物價壓力更多來自於需求端,供給端壓力比前兩輪小很多。第二產業對本輪低通脹的貢獻只有48%,遠低於1998的57%和2015年的100%。但當前服務價格降至歷史最低水平,2024年甚至有3個季度負增長(歷史首次),代表着需求端的價格壓力比供給端可能更大。
2、從歷史經驗來看,價格周期的不同特點,決定了走出低通脹的不同模式:1998年是“去產能+促消費”雙管齊下,2015年是去產能爲主,促消費政策力度小。1998年和2015年低通脹的成因並不完全相同,盡管工業價格下降都是主因,但1998年最大的就業部門價格下降(第一產業佔就業的50%),引發價格和需求的負反饋循環。爲了打破負循環,1998年促消費政策力度極大,用於居民增收的財政資金佔到GDP的1.2%和財政收入的9.4%,相當於今天的1.6-2.1萬億。2015年物價下行主要來自工業,而服務業漲價強勁,使得勞動工資上漲和低通脹並存,消費仍維持相對強勁。
3、當前應如何走出低通脹:雙管齊下,促消費比去產能更重要,促消費政策需要“加強版的1998年”。假設採取去產能政策,使得短期工業價格在2024年的基礎上回升2個點,GDP平減指數將從2024年的-0.7%回升到-0.02%,仍不足以走出低通脹;但如果促消費政策力度更大,使得服務價格回升2個點,GDP平減指數將從-0.7%回升到+0.39%,加上消費回暖帶動的商品價格回升,最終GDP平減指數還會更高。從實踐來看,需要“去產能”和“促消費”雙管齊下,後者更重要。並且考慮到服務價格降至歷史最低水平,促消費政策力度可能需要比1998年更強。
風險提示:(1)歷史比較可能忽略一些因素,比如除了產能政策和消費政策外,1998和2015年擴投資、房地產等政策也發揮了很大作用。(2)影響價格的因素很多,除了政策發力之外,還有很多因素是無法把控的,如國際油價的變動,還有供給端豬周期的變動、氣候因素的影響等等。(3)需要注意到政策的成本問題,促消費政策要拉動物價回升,可能需投入的資金量較大,並且可能像美國一樣出現通貨膨脹的惡果,這是需要警惕的風險。
正文
1. 物價下降的成因:歷史並非簡單重復
1.1. 1998和2015年兩輪低通脹的成因不同
過去幾輪低通脹有何相同和不同之處?我們可以從三大產業的價格指數(平減指數)來看,第一產業平減指數與食品CPI基本一致,第二產業平減指數與PPI基本一致,第三產業平減指數自2014年以來與服務CPI較爲一致。
工業價格驅動整體物價下行,1998和2015年兩次GDP平減指數轉負,工業價格能解釋57%和100%,這說明供給端的產能壓力是兩次低通脹的主要原因。1998-1999年,GDP平減指數連續7個季度負增長,同比增速從+1.2%降到-1.4%,下降2.6個點,其中1.5個點,即57%來自於第二產業平減指數,只有0.8個點、21%來自於服務業價格下降。2015年,GDP平減指數連續2個季度負增長,同比增速從+0.7%下降到-0.2%,下降0.9個點,其中0.9個點、約100%的降幅來自於第二產業,服務業價格在此期間沒有下降。
但是,前兩輪低通脹期間的消費表現是完全不同的,1998年的低通脹背後有更多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2015年消費相對強勁,需求端房地產銷售和投資走弱。
1998年的消費需求不足,體現爲價格和需求的負反饋循環。這個負反饋循環包括以下四步:
(1)價格下降,並且降價覆蓋了七成以上的就業行業。分行業來看,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價格下降比較明顯,這兩個產業佔就業比重在70%以上。第一產業方面,食品CPI從1997.8-2001.3連續44個月同比負增長,而農林牧漁就業佔50%左右,“谷賤傷農”,對農村居民收入影響較大。第二產業方面,PPI從1997.6-1999.12連續31個月負增長,工業就業佔比約23%。
(2)企業利潤減少。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受影響較大,第一產業名義GDP增速1998-2000年平均僅爲1.1%,其中1999年負增長,遠低於整體經濟增速;第二產業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1998年下降17%,虧損面達34%。
(3)就業和工資壓力加大。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998-2000年平均增速僅爲2.5%,而農村人口彼時佔比約65%。城鎮方面,非私營單位1998年工資總額僅增長0.2%。
(4)消費需求走弱。社零增速從1997年的10.2%驟降至1998年6.8%。GDP最終消費支出裏,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在1998-1999連續兩年負增長,增速分別爲-0.58%和-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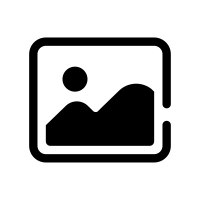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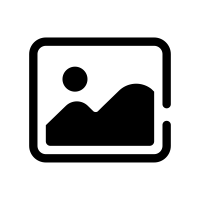
相比之下,2015年雖然房地產銷售和投資面臨壓力,但低通脹並沒有傳導到收入和消費,反而是勞動工資上漲和低通脹並存。
這是因爲2015年的物價下行主要來自工業,而服務業漲價強勁,2015Q3-Q4二產平減指數-5%,三產爲+4%。經過了十多年的經濟結構轉型,此時服務業已經成爲最大的就業池,2015年佔就業的42.3%。因此工業價格下降、服務業價格上漲,對於勞動工資漲價具有積極意義,從而能夠維持消費需求的相對強勁。2015年社零增速雖然從12%小幅降至10.7%,但仍然遠高於當年7%的經濟增速;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從上年的56.9%提高至69.3%。這跟1998年的低通脹是完全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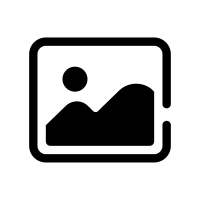
1.2. 這次不一樣:服務價格降至歷史最低水平
這輪低通脹表現與前兩輪不完全一樣,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工業對整體價格的影響是最小的,二是服務業價格降到歷史最低水平。前者意味着,工業領域產能過剩壓力小於前兩輪,後者意味着存在價格和需求的負反饋循環壓力。本輪低通脹期間,GDP平減指數下降2.2個點,其中48%來自二產,是歷次低通脹中第二產業貢獻最低的一次,1998和2015年分別爲57%和100%。服務業價格降至歷史最低水平,本輪低通脹期間平均爲0.2%,2024年有三個季度出現負增長。
需要注意的是,房地產對服務價格影響很大,但即使剔除房地產,當前服務價格也下降到了歷史最低水平。服務價格(三產平減指數)在24Q1-Q3出現連續三個季度的負增長,平均-0.08%,其中房地產業的貢獻爲-0.32%,剔除房地產後其他行業爲+0.24%,仍然是歷史最低水平,此前低點是在1999年Q3的+0.76%。
因此,本輪低通脹某種程度上和1998年更相似,最大的就業部門出現了價格增速的明顯下降。第三產業已經成爲當前最大的就業池,佔全社會就業比重達到48%左右(2023年數據)。所以,本輪低通脹和1998年更相似,最大的就業部門價格增速下降,1998年是農業,當前是服務業。1998年價格下行形成負反饋壓力,即“價格下降→就業和收入壓力加大→消費需求走弱→價格下降”,這個壓力在本輪低通脹期間仍然存在。
所以,當前價格環境下,走出低通脹政策需要“加強版的1998年”。去產能政策可以帶動工業價格的回升,但不足以拉動當前低迷的服務價格,因此走出本輪低通脹,去產能政策不可或缺,但通過刺激需求拉動服務價格也必不可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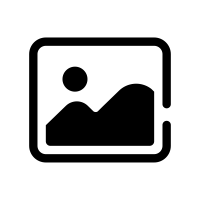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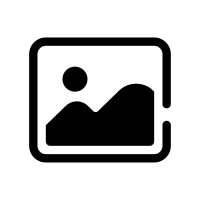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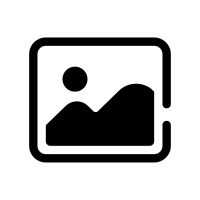
2. 走出低通脹:1998和2015的兩種模式
由於價格周期的表現不同,1998年和2015年走出低通脹所選擇的是兩種不同的模式,1998年是“去產能”和“促消費”雙管齊下,2015年主要是去產能,促消費政策力度較小。
2.1. 1998年:“去產能”和“促消費”雙管齊下
2.1.1. 去產能:以紡織業爲突破口
1998 年的去產能政策並非獨立开展,而是與國企改革聯系在一起的,目的是爲了通過行政手段去產能,實現國有企業經營效益的提高。這一時期的政策可概括爲“鼓勵兼並,規範破產,下崗分流,實施再就業工程”。通過“抓大放小”、“下崗分流”等政策,國有企業實現了一輪大規模產能出清,國有企業數量從1995年的11.8萬減少至2000年的4.2萬,減少了64%。國企盈利面在1998年只有31.3%,這意味着近七成國企是虧損的,但去產能帶來了經營績效的提升,2002年盈利面开始超過50%。
從行業來看,當時各行業都涉及產能結構優化,其中紡織業是突破口。1997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指出“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本世紀末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明年要以紡織行業爲突破口,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努力使部分企業經營狀況明顯好轉”。
[1] 199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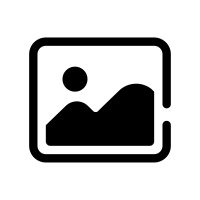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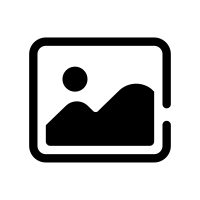
2.1.2. 促消費:大力推進居民增收
這一輪促消費政策集中在1999年出台,主要包括以下政策:
一是通過各種方式引導居民存款分流到消費和投資。1999年上半年,在消費承壓的同時,居民儲蓄存款的增速明顯反彈。爲了促進儲蓄到消費的轉換,採取了以下措施:
(1)存款利率降低一半。考慮到跟隨貸款利率調整,以及引導存款流出促進消費,從1998-1999年,央行四次調降存款利率。到1999年下半年,各項存款利率降低到1998年的一半左右。如活期存款利率從1.71%降至0.99%,5年期定存利率從6.66%降至2.88%。
(2)對存款利息徵收20%的個人所得稅,進一步刺激存款流向消費。1999年11月开始,對居民存款徵收20%的個人所得稅,存款收益率進一步下降。國稅總局指出“恢復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徵收個人所得稅,可以引導城鄉居民分流一部分儲蓄資金,鼓勵消費和投資。”
二是鼓勵消費信貸的發展。中國人民銀行1999年3月發布了《關於开展個人消費信貸指導意見》,开始允許所有中資商業銀行开辦消費信貸業務,並要求1999年擴大消費信貸規模、开發新的消費信貸品種。1999年,工商銀行在原有的3種消費信貸基礎上,新推出了7種消費信貸品類,形成了10大品種體系,面向購房、購車、旅遊等多種消費行爲。
三是大力增加居民收入。
總量資金:增收的財政支出半年540億,年化1080億佔當年財政收入的9.4%、GDP的1.2%,相當於今天的1.6-2.1萬億。按GDP換算到今天,135萬億*1.2%=1.6萬億;按財政收入換算,22萬億*9.4%=2.1萬億。
增收對象:五類群體8400多萬人。①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②失業保險;③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④提高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⑤提高離退休金。
具體來看,在提高薪資方面,1999和2001年連發兩文。國辦發〔1999〕78號:從1999年7月1日起,將機關行政人員基礎工資標准由每人每月110元提高到180元,級別工資標准由十五級至一級每人每月55元至470元提高到85元至720元。
國辦發〔2001〕14號:從2001年1月1日起,機關行政人員基礎工資標准由每人每月180元提高到230元,級別工資標准由十五級至一級每人每月85元至720元提高到115元至1166元。在調整機關行政人員工資標准的同時,適當調整機關工人的崗位工資和技術等級(職務)工資標准。機關工人的獎金部分按照其在工資構成中的比例相應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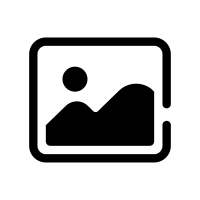
四是增加節假日,爲假日消費創造條件。9月末國務院對《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作了修訂,全國法定節日放假時間由七天增加到十天,爲促進假日消費創造條件。
五是取消消費限制。各級政府部門开始清理和取消在通貨膨脹期間出台的抑制消費需求的過時政策,如部分地區此前不允許個人和家庭購买汽車,1999年陸續放开;以及二手房交易也在一些大城市放开。
六是擴大高校招生。1999年,國家決定高等教育在原定招生計劃的基礎上擴大招生規模33.1萬人,使全國的招生規模擴大至153.7萬人。
七是改善消費環境,提升消費信心。
事後來看,這輪促消費政策起到了擴大消費需求的作用。居民消費支出增速在1998年降至6.1%,基本見底,隨後2000年回升到12.1%。消費傾向也從1998年的68.9%持續回升到2002年的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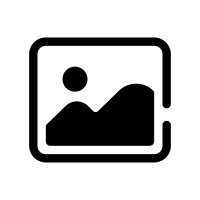
2.2. 2015年:“去產能”>>>“促消費”
2015年的去產能政策可以分爲5個步驟:
一是明確任務。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提出按“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辦法推進去產能,制定配套政策,依法推進市場化破產程序,落實財稅支持等政策,控制增量防止新產能過剩。
二是聚焦重點對象。2015年12月9日國常會,中央層面首次提出僵屍企業問題,明確對不符合相關標准和長期虧損的產能過剩行業企業處置方式,要求到2017年末實現經營性虧損企業虧損額顯著下降。
三是細化行業政策,分行業的去產能政策出爐。2016年2月,國務院分別發布煤炭、鋼鐵行業去產能意見,規劃去產能規模、時間,推動行業結構優化升級。同年6月、7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有色金屬、石化產業調結構促轉型增效益指導意見,化解產能過剩,提升產業發展質量。
四是加強環保協同。2016-2017年开展4次中央環保督察,輔助鋼鐵、能源、化工等行業去產能,通過立案調查、處罰、拘留等多種整治措施,淘汰落後產能。
五是金融政策持續完善。2009年起抑制金融資源投向產能過剩行業,要求對不符合條件項目不得授信,從嚴審查產能過剩產業項目貸款。2016年9月,國務院印發降低企業槓杆率意見及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指導意見,通過多種方式降槓杆,以市場化債轉股助力優質企業渡難關。
相比之下,2015年也有一些促消費政策,但力度要小於1998年。
一是提高薪資。2015年1月,國辦發[2015]3號文[1]提出從2014年10月开始,調整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工資標准,相應增加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離退休費。
二是優化休假安排。2015年8月,國辦發〔2015〕62號文[2]指出要落實職工帶薪休假制度、鼓勵錯峰休假、鼓勵彈性作息。
三是促進消費升級、優化消費環境。2015年11月,國發〔2015〕66號文[3]指出,要更好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並通過完善質量監管體系、健全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等措施改善消費環境。
整體來看,2015年由於消費需求並沒有像1998年一樣明顯下降,這輪促消費政策力度是遠小於1998年的,價格回升更多依賴於“去產能”。
[1]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關於調整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工資標准和增加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離退休費三個實施方案的通知-組織與人力資源處
[2]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促進旅遊投資和消費的若幹意見_旅遊_中國政府網
[3] 國務院關於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__2015年第34號國務院公報_中國政府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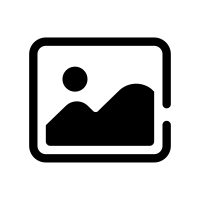
3. 價格回升的兩種模式:“二產+2%”與“三產+2%”
由於去產能和促消費政策的組合不同,1998和2015年物價回升的路徑也不一樣。1998年這輪GDP平減指數的回升,72%來自第二產業價格貢獻,21%來自服務價格,7%來自第一產業。而2015年價格回升中,99%都來自第二產業。
當前應如何走出低通脹:雙管齊下,促消費比去產能更重要。假設採取去產能政策,使得短期工業價格在2024年的基礎上回升2個點,GDP平減指數將從2024年的-0.7%回升到-0.02%,仍不足以走出低通脹;但如果促消費政策力度更大,使得服務價格回升2個點,GDP平減指數將從-0.7%回升到+0.39%,加上消費回暖帶動的商品價格回升,最終GDP平減指數還會更高。從實踐來看,需要“去產能”和“促消費”雙管齊下,後者更重要。
促消費政策需要“加強版的1998年”。1998年這輪低通脹期間,服務業平減指數從1998年底的3.9%快速下降到1999年Q3的0.79%,但到2000年Q1开始就回升到3.5%以上,促消費政策對服務價格的提升較爲明顯。考慮到當前服務價格下行的深度和廣度都超出1998年前後,促消費政策需要更大力度,才能帶動服務價格回升。
消費政策還有哪些空間?一是將消費補貼範圍擴大到服務消費,最直接提振服務需求。二是加大收入補貼力度,如生育補貼、農村養老金、失業保險等方向。三是大力促進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24Q4房地產行業平減指數實現了5個季度來的首次正增長,但近期房地產市場再次走弱,年中或需要政策再度接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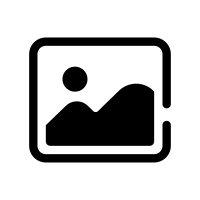
4. 風險提示
(1)歷史比較可能忽略一些因素,比如除了產能政策和消費政策外,1998和2015年擴投資、房地產等政策也發揮了很大作用。(2)影響價格的因素很多,除了政策發力之外,還有很多因素是無法把控的,如國際油價的變動,還有供給端豬周期的變動、氣候因素的影響等等。(3)需要注意到政策的成本問題,促消費政策要拉動物價回升,可能需投入的資金量較大,並且可能像美國一樣出現通貨膨脹的惡果,這是需要警惕的風險。
注:本文爲自東吳證券研報《走出低通脹:“去產能”和“促消費”誰更有效?》,分析師:蘆哲S0600524110003、佔爍S0600524120005
標題:走出低通脹:“去產能”和“促消費”誰更有效?
地址:https://www.iknowplus.com/post/2059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