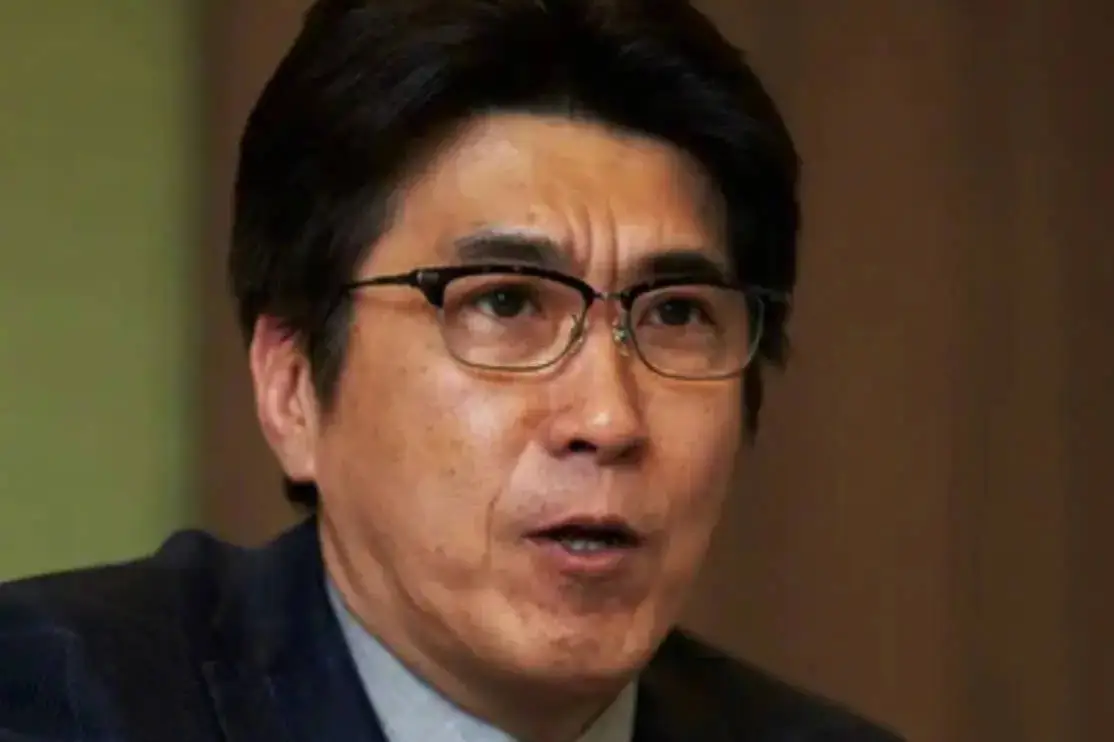收視破4、討論聲量有限,《六姊妹》式“電視特供劇”爲何成了行業香餑餑?
搜狐娛樂專稿(胖部/文)
作爲今年的央視开年劇,《六姊妹》毫無疑問地“響”了。
根據酷雲數據,該劇首播收視率破3,此後多日平均收視率均在3%以上,到2月11日該劇更是平均收視直接破4,如此成績甚至在近幾年都不多見。

而在網播端,超過28000的站內熱度對於一部年代劇來說,也達到了熱門劇的標准。
問題在於,如此播放熱度卻沒有獲得相應的討論,在網絡傳播端該劇的存在感可謂極低,既缺乏正面出圈的話題和橋段,也缺乏足夠的熱搜支持。
如此數型,很容易讓人想到所謂“電視特供劇”,或更直接的“父母特供劇”。那《六姊妹》算是一部“特供劇”嗎?這門生意又是憑什么,成了行業公司的新選擇?
憑什么“火”?
目前圍繞《六姊妹》的主要話題,或許是該劇的選角問題。
不少觀衆开始討論,由全員年齡40+的陣容出演青少年時代,真的有必要嗎?尤其是女主演梅婷和出演其父母的劉鈞、鄔君梅年齡差較小,放大了部分觀衆的不適感。

更深層次的問題或許是,觀衆對演員和角色貼合度的不滿,也源於角色本身缺乏生命力。
在社交媒體的討論中也有聲音指出,《六姊妹》整部劇前半段的話題,基本就是給姐妹們解決兩大問題——找對象、找工作,而親情的表現則是在這兩方面的相互惦記或寬容。如此內容對於當下的不少觀衆來說或許缺乏吸引力。
制片人彤彤對搜狐娛樂分析稱:“選角問題如果沒有明顯的表演災難,那么大概率角色本身是存在問題的,畢竟有個概念叫‘戲捧人’,如果角色本身足夠精彩、觀衆能被帶入,外形上的一些問題其實是可以含糊過去的。”
不過她認同,盡可能貼近演員外形是選角工作的關鍵,“如果觀衆發現某個角色外形不符合,那么排除場外因素,一定是演員本身的某些要素吸引了團隊,比如其是否自帶流量、或能吸引某一類觀衆以及能給劇集帶來某種標籤?”

對於《六姊妹》來說,選角本身或許恰恰體現了在這些方面的一些思路。
劇集策劃曹璐表示理解:“其實從《六姊妹》的選角能夠看到,這套班底能讓哪怕對娛樂圈不夠了解的群體,也會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主創希望給觀衆的印象就是‘大制作’,這在前期宣傳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所謂的‘國民度’,就是在非娛樂受衆之外也能具有影響力,這樣的明星在行業過去十多年主打流量經濟之後,甚至可以說是稀缺資源。現在還能湊出一套有國民度的85、90後陣容嗎?一是選擇太少,二是整部劇的預算會非常嚇人的。”
除了選角之外,《六姊妹》本身的選題和制作,都凸顯了對電視端觀衆的友好。
年代劇本身一直是電視端的寵兒,再現中老年曾經親歷的時代事件、生活場景甚至具體經歷,對年齡、圈層更多元的電視受衆是極具吸引力的。
《六姊妹》也正是如此,從60年代支援建設造成的家庭遷移、單位辦公室裏的家長裏短、一家人爲喫飯發愁等等細節,穩住了前期的觀衆好感;具體到姊妹們婚戀、工作、生活的不同選擇,更能推動不少觀衆想起個人經歷、帶動家庭場景的討論。

而如果故事和人物能夠出彩,還能吸引家庭場景下的更多年輕受衆入坑。
曹璐分析稱:“從《小巷人家》的火爆可以看到,打造舊時光裏的人情美,對當下年輕人其實是有治愈屬性的。這也是目前很多劇集處理角色的模式,希望打通類似年代家庭劇對年輕觀衆的吸引力,但就有個前提,故事和制作要過關。”
這也是《六姊妹》試圖吸引年輕人伸出的一根觸角,比如相較原著,一家人的設定都有更正面的呈現,比如老太太何文氏及母親劉美心等,重點強化一家人的情感加成。
但無論選角還是題材再到制作,這依然是一部有着一定“定制”意味的劇集,相對更貼合跨年齡層、多圈層受衆需求,也更容易引爆電視端數據。這和過往行業主要針對主流年輕受衆制作內容的選擇,明顯形成了差異。
而這樣的選擇,這幾年並不少見。
新選項
在2022年之前,電視劇和網絡劇始終處於一個越來越趨同的過程。伴隨着視頻平台逐漸掌握更多制作資源和行業話語權,台網聯播逐漸成了行業許多頭部項目的標配,甚至平台自、定制項目也紛紛“上星”。
不過近兩年有不少劇集,反而开始回歸如何創造高收視率的邏輯,而非以往優先選擇打开主流受衆的思路。
尤其是一批年代、家庭或革命战爭題材劇,出現了一定的台播、網播熱度倒掛,或台播熱度帶動網播的情況,比如去年的《煙火人家》《好運家》《上甘嶺》《好團圓》,以及前年的《人生之路》《我們的日子》《父輩的榮耀》《珠江人家》《冰雪尖刀連》等等。

“一個前提條件是,網播的受衆圈層越來越多元了。”制片人文偉指出。
“這就給一些電視端的熱劇創造了台播帶動網播的空間,過去中老年人中途开始看一個劇,可能要等二輪才能看全,現在發現一個劇他們也到網上去補前面的劇情,這就加強了台網聯動的效應。”
同時,文偉認爲這與前兩年主流劇集的熱度有關,“行業會看到年輕觀衆越來越开放,一些主旋律劇、年代劇只要拍得好,比如《山海情》《人世間》等同樣可以成爲行業爆款,在流量劇基本盤下滑的當下,這成爲平台的調整方向,也吸引大量流量演員選擇這些內容轉型。”

彤彤則指出,這主要是因爲長視頻平台降本增效之後的行業環境。
“行業公司收益更多地和網播熱度掛鉤,再想靠着迎合平台旱澇保收,已經不可能了。而現在的市場環境是,大投入的網劇未必就有好的回報,甚至‘踩空’概率很大,那么很多公司會調整供應方向。”而相對來說,電視台上的“大劇”往往還能獲得不錯的熱度。
她也指出除了公司,很多平台爲了擴大營收,也會尋求自制內容“上星”,版權收入的佔比越來越高。去年的《繁花》《與鳳行》《慶余年2》《長相思2》《我的阿勒泰》《玫瑰的故事》《大奉打更人》等熱門劇基本都是台網同步开播。

而這也推動着,行業的制作內容會更多地偏向於電視端審美,甚至有一定的“定制”。
“比如演員陣容的國民度,或者至少是老百姓認識的‘熟面孔’,這會增強觀衆對劇集制作體量的認知;再比如類型上,年代劇或者更多講述代際關系的家庭劇,這兩年的頭部項目明顯在增加。”曹璐表示。
她還特別指出,《六姊妹》主打的“全女”劇集,這兩年也成爲常態,比如講述三代女性的《煙火人家》、聚焦三姐妹家庭的《好團圓》等女性群像劇,其數據反饋甚至會優於網播端的年輕人市場,“畢竟對於大多數家庭場景,遙控器依然掌握在女性手中。”
好生意?
如今,尋求在電視端獲得更好的收視反饋,已經成爲多數行業內容,甚至是平台自制內容要考慮的問題。
文偉透露,目前一些平台自制劇遲遲不开播,也存在要蹲電視台排期的情況,“有些流量向的內容可能不會這么操作,但比如年代劇、家庭劇,哪怕是都市劇、懸疑劇這些,都會積極爭取一下能否‘上星’。”

在這個層面上,他覺得放大電視端“定制”屬性已經是行業常態,“做純粹的網劇太難了,如果依然是平台高價收劇、公司旱澇保收的狀態,大家還會快樂地去拍偶像劇,但現在,公司必須在愈發擁擠的流量市場之外打开機會。”
“那么,能夠打开電視端聚集的‘沉默的大多數’,同樣是極具價值的。”
所謂“沉默的大多數”,即在愛互動、愛表現的年輕主流受衆之外,更多地在沉默看劇而缺乏網絡聲量的多元年齡圈層。他們能夠給劇集帶來的網絡傳播相對有限,但過往的例子也反復證明着,這個群體的基數或許更加驚人。
能夠打動這個圈層,未嘗不是一種好生意。
但反過來看,這或許本質上是對目前長視頻內容升級困境的一種“逃離”。
“其實電視台的議價空間還是比較有限的,”彤彤透露,“如果能在視頻平台有爆款,那收益肯定要多不少,但問題是,誰也不敢說自己的劇一定能播好。那么,旱澇保收的生意幹嘛不做。”
當然,更好的方案是在台網兩側都能有不錯的回報,“《人世間》《繁花》《小巷人家》等其實證明了,好的故事和人物加上更當下的價值觀,年代劇也是能夠打動年輕觀衆的。所以這種放大電視端受衆偏好的選擇,未嘗不是打开更多可能性的一把鑰匙。”

目前,各平台發力的類似內容不在少數。其中非常值得關注的,是一批久違了的歷史正劇,如《太平年》《風禾盡起張居正》《陽明傳》《大漢賦》等。
年代劇、家庭劇方面,還有楊冪、歐豪主演的《生萬物》,白鹿、歐豪、翟子路的《北上》,梅婷、田雨、陳昊宇的《好好的時代》,張國立、佟大爲、梅婷的《老爸去相親》,亦舒IP改編劇《歡聚》,周雨彤、吳越出演並與最近定檔的《180重啓計劃》等。
“更重要的可能是,無論台播劇還是網劇,創作者需要走出跟風式、套路化的創作思路,真正拿出一些有靈魂的故事和人物。”曹璐認爲,“在今天這個時代,不應該再出現家長愛看、孩子批判的內容。”
如何制造台播熱劇,上一個行業版本已經有了明確的答案,而在當下,如何通過行業的自我升級打造具有各圈層共識的好劇,或許是需要如《六姊妹》這樣的大劇,更好完成探索的方向。
標題:收視破4、討論聲量有限,《六姊妹》式“電視特供劇”爲何成了行業香餑餑?
地址:https://www.iknowplus.com/post/193025.html